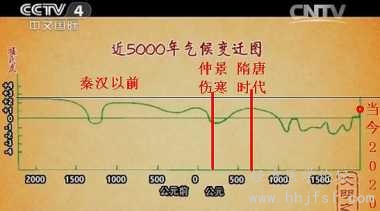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
本帖最后由 汤一笑 于 2022-2-17 12:20 编辑
甘草之迷(修订稿)
本文曾在《经方》杂志微信版20210827期首发
汤一笑
一、 泛用之迷
日本学者冈田研吉等人研究认为宋代以前,中土狭义伤寒的治疗存在以阮河南为代表的苦酸派和以张仲景为代表的辛甘派这两大学术派别。唐以后则苦酸派消沉而辛甘派独兴。所谓辛甘,无非指好用姜桂草枣之类,从仲景方用药的频率看,甘草排第一,姜(生姜+干姜)第二,桂三,枣四(其实我觉得汤剂中最常用的药物应算是热水)。甘辛为首,确实如此。而在目前出土的汉代医学简帛资料中,东汉末以前,除去酒、醯之类,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却是桂、姜、椒、乌喙之类,罕见甘草。我一直好奇汉末仲景方为何突然如此泛用甘草?调味?调和诸药?解毒护胃?
南朝陶弘景称甘草为药之“国老”,且“最为众药之主,经方少不用者”。但在目前所见出土的早于仲景方的秦汉医简中,甘草并不如后世那么常用。《万物》中找不到甘草。南方的马王堆《五十二病方》283方中甘草5见。连北方的《武威汉简治百病方》36方中,甘草也仅3见。当时甘草的效用似乎更多的跟止痛、愈合伤口有关,可能是一味重要的外科用药。《内经》十三方中不见甘草。《范子计然》的商品药材中没有提到甘草(或文佚)。西汉史游《急就章》中则有了甘草(公元前40年左右)。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西部所出土的伤寒方中都没有用到甘草。如《武威汉简治百病方》的“伤寒逐风方”、“治鲁氏青行解腹方”(唯一麻黄方)、《居延汉简》的“伤寒四物”方、《敦煌汉简》的“伤寒方”,都是散剂,都没有用到甘草,而西域显然是不缺甘草的。这些西域汉简的年代大约都在两汉之交时期。何以会在汉末的仲景伤寒方中出现了泛用甘草的现象?以至陶弘景说“经方少不用者”。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从以上史料粗略判断,甘草在汉方中的泛用应该是从东汉开始的,而且很可能是随同当时西来麻黄类方的兴起连带发生的。(可参见《麻黄西来及其他》一文,汉医方泛用麻黄大约也是发生在东汉偏后期)
因为甘草泛用的问题,我特意研究了汉医学的“邻居”:印度医典《妙闻集》(公元前6世纪至元3—4世纪)、《医理精华》(约公元650年)和藏医经典《月王药诊》(约公元750年)。印度医学的经典《阇罗迦集》地位相当于汉医学的《素问》,约公元1—2世纪成书,也偏于内科,但彻底追求药物疗法,不同于《内经》重针灸。这些不同医学文化的典籍,除《妙闻集》、《阇罗迦集》外,因为年代较晚,不可能对东汉汉医学产生什么影响,但可用于考察异族传统医学的一些特点。
《妙闻集》是印度传统医学三大经典之一,妙闻氏,据说是公元前6世纪的人,但一般认为此书虽早有流传,但最终修订完成于公元3—4世纪。《妙闻集》偏于外科,外科医术方面高超。《妙闻集》第一卷第38章名为“药物汇类”中有37个族(族表示功效相同的药物 即37类),甘草共在8族中都出现(第13、15、17、19、20、23、24、26族),也属于泛用者,这8族药物,大略功效有:净化和增产母乳、治下痢、治动悸、增精力、使体肥、治大出血、消毒(第20族)、治热病、治创疡、疗渴、治心脏病等。但在《妙闻集》第一卷第39章《净化剂和镇静剂》中,分述了吐剂、下剂、吐泻剂、头部净化剂、镇静剂七类所包含的重要药物,其中并没有甘草,可见甘草并不属于重要的药物。印度传统医学所用的甘草为欧甘草(光果甘草)。
《妙闻集》第一卷第45章为《液体的用法》,其论八种蜂蜜,有减肥功效,“以所有蜂蜜皆成于种种物质,故作为使药胜于其他”,但同时又禁止蜂蜜与温热性药剂或天水一起使用(因蜜皆混有毒)。又论十二种甘蔗汁、蔗糖浆及蔗糖,能净化血液,治疗大出血、治渴、抑制焦热感。《妙闻集》第一卷第45章、第26章,有讨论味的分类以及理论,认为味有甘酸咸辛苦涩六种,而水是此六种味的母体,其中偶尔提到甘味能抑制毒素,但似乎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功效。《妙闻集》第一卷第43章《论吐剂的制法》中,药液多要加入蜜和盐饮用;第44章《论下剂的制法》中,下剂也多使用“糖浆”为使药,则可知药剂中配糖是印度传统医学的一个传统,这在后世的《医理精华》中就更明显了。
参见廖育群《 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医理精华》的医药有很多与汉医学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糖是常用药,使用频率很高。如认为陈的砂糖,是最好的去胆汁药,能使血变纯。如常在治疗热病的汤液中,加入粗糖,则可去风热。《医理》有一类专药叫药糖剂,即方剂药物中加入大量的糖或蜜,又叫练药。干渴治疗都用药糖剂。以白糖、蜜、硫化铁粉,制成药糖剂,则可解毒。印度医学好用糖可能与印度制糖技术发达而糖易得有关。《医理》中也用甘草,但不泛用。其用:退热的灌肠剂中常用;甘草与芝麻油合制通便剂;甘草加蜜灌鼻治打嗝;甘草酥煎灌鼻疗头痛症;糖水冲服甘草粉疗胆汁性心脏病;外科丹毒、伤口治疗、眼病中多用到甘草;等等。但在解毒剂(动物毒、植物毒)中,甘草并不重要。
藏医受印度医学的影响很大。《月王药诊》中的散剂中多加糖。又专有一种糊剂,加蜂蜜和糖为糊内服。糖似乎类似药引之流。《月王》的解毒剂中基本不用甘草,但常配糖、蜜。解合成毒中毒的药剂必须配糖。蒙医也受印藏医学的影响较大,如今的蒙医标准散剂,寒凉药剂要加适量白糖,温热药剂要加适量红糖。
陈明先生在《印度佛教医学概况》中对律藏医药有初步概括,指出佛教僧团中最常见的疾病是风冷热三种,而其最常见的药物是酥、油、蜜、石蜜、糖等,均属于七日药(仅可服用七日)。《摩诃僧祗律》卷17记载了几种治病之方:热病/酥;风病/油(摩膏之类);水病/蜜;乾屑病/石蜜;冷/石蜜、酪;下病/乳;下吐/鱼汁、肉汁。
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印度一带已经能够制造蔗糖。因印医、藏医方剂好用糖,而印度的“西国石蜜”早在汉代就传入中土,为珍贵之物。因此我有点怀疑,仲景方泛用甘草,是不是受了印医药剂好配糖以及以糖解毒净化身体的影响,但因中土少砂糖而以甘草代替?但当时中土虽少砂糖却是有饴糖的,又或是汉末社会战乱,饴和蜜都极珍贵难得?我国民族医药中,壮医学有用甘蔗解毒法,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西南丹土人打仗时总是随身携带一节甘蔗,一旦中毒箭,则吃甘蔗能缓解毒性发作。此法起源于何时则不得而知,糖在壮族民间也是通用解毒剂。唐高祖时期的刺史席辩(约619年)得岭南俚人解毒秘方药“ 初得俚人毒药且令定方。生姜四两,甘草三两,炙,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旦服三服,服讫,然后觅药疗之。”岭南俚人此法不知是土人古法还是学自外族?而草姜二药正是仲景方中使用频率最高之类。但南方不产甘草,岭南俚人解毒所用“甘草”不知是国老甘草还是南方 甘草藤?北宋王谠《唐语林·补遗四》:“ 甘草非国老之药者,乃南方藤名也……以条叶俱甘,故谓之 甘草藤,土人但呼为‘ 甘草’而已。”但按席辩的说法,“知其药并是常用”,应该就是普通常用的甘草。
汉方的本草写作有个特点,就是一上来必说有毒无毒。而印度的本草就没有这特点。汉方的本草为什么会这样呢?药物的发现,大多还是跟自身的食物和获取食物有关,也有些是跟其他动物学来的。人或动物误食某些动植物会中毒,人类也会利用这些知识治疗或捕食,比如利用有毒植物杀虫、镇痛、毒鱼、制作毒箭捕杀动物等。由于误食、误伤或动植物伤害,人类自然也有解毒的需要,在漫长的进化发展中,解毒药也会发明出来,前述岭南俚人的解毒药应是如此而来。也许正是汉方传统上重视药物的性质有毒无毒以及解毒药物,才将甘草这样的解毒药物推到了极重要的地位?
汉方医学中,将甘草视为解药毒之药不知始于何时。西汉前期《淮南子 览冥训》言“今夫地黄主属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淮南王刘安生活时代为前179年-前122年,此时甘草突出的功效似乎并非解毒而是“生肉”。但在尚志钧先生辑复的西汉《神农本草经》中(尚氏认为书成于约公元前35——公元5年),甘草的功效“长肌肉”和“解毒”已经并存。前文已有判断,甘草在汉方中的泛用应该是从东汉开始的。甘草解百药毒的新功效大概也是在东汉时期才深入人心的,而且甘草这个新功效并非是其他域外医学文化传播的,而应是本土学术的发明。
尚志钧辑复本《神农本草经 甘草》(西汉末年):“味甘,平,主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疮,尰,解毒。久服轻身,延年。生河西川谷。”
陶弘景《本经集注 甘草》(约成书于5世纪末):“味甘,平,无毒。主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疮,尰,解毒。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为九土之精,安和七十二种石,一千二百种草。久服轻身,延年。一名密甘,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草。生河西川谷积沙山及上郡。”
后者增加的内容,大概主要来自东汉的《名医别录》,增加的内容主要是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安和众草石。
《金匮玉函经》卷一《证治总例》云“张仲景曰,若欲治疾,当先以汤洗涤五藏六腑,开通经脉,理导阴阳,破散邪气,润泽枯槁,悦人皮肤,益人气血,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证治总例》学者或认为是六朝医家所撰,或认为仲景原著,各有说辞。但此“张仲景曰”一段却很有可能真是仲景所论。这是论何以用汤剂,但若对比此论与《本经集注》甘草条文之效用,涤荡五藏六腑寒热邪气、开通经脉、润泽枯槁、益人气血、净万物,两者何其相似,何以如此巧合?甘草为“九土之精”,而“水者,地之血气”(《管子.水地》),仲景方中最泛用的两味药热水和甘草的基本效用其实相类。或许可视此为仲景对经方泛用甘草的解释?称甘草为“水药”未为不可。治疗伤寒是从治疗热病发展来的,汉医学早期治疗热病是重视补水的(这是朴素的思想),《素问·刺热篇第三十二》:“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应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可见在素问时代,医经派治疗热病除针刺外,还重视饮水的,而这种理念后世却消失了。《伤寒论》治疗热病用汤药,不知是不是上古热病治疗重视饮水传统的发展?现在感冒西医也叫多喝水。
水之为药,汉医学一贯缺乏这种意识,或是熟视无睹。而在讲究“净化”的印度阿育吠陀中,水正是神药之一,传说梵天王教给人类的第一种药物就是开水。其古典《梨俱呔陀》(亦译为《赞诵明论》),其中很多诗句都是赞颂香药水及水的治疗力量。阿育吠陀认为水是六味的母体,或者说水蕴含六味。具体治疗上,开水:治疗发烧、哮喘、减肥、去风、去痰。凉开水,去三种体液。同样的水,放一天后却变成会增加体液。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云“水及梨皆是天药”。我国蒙古族民间也有谚语云:“病始于消化不良,药始于开水”。据我所见,印度古典吠陀医学(《妙闻集》、《阇罗迦集》)中,药物剂型多种多样,虽在吐、泻法中也见有煎煮汤剂,但内服并不以汤剂为特色,也非主流。
从方剂时代变化的角度,仲景方有两个比较特异的地方,一是泛用汤剂;二是泛用甘草。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105年)论“经方”一段中有“致水火之齐”的说法,但不知是西汉末方技整理者侍医李柱国所论还是东汉班固所论。研究者稍留心《伤寒论》之前原始中医方剂资料(目前主要就是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等)就能发现,就目前掌握的可靠史料来看,《伤寒论》之前的内服剂型似乎是以散丸剂为主流,“饮药”多是以酒、醋、白饮之类送服,汤剂还未盛行。朱晟先生认为东西方最古的剂型都是散剂。汉初的仓公医案用药,内服除下气汤、柔汤为汤剂外,火齐米汁饮、火齐粥、火齐汤之类应该都是滑粘之液,与《伤寒论》汤剂不同(后世汤求清),还算不上标准的汤剂。还可以比较一下汉末华佗和张仲景的疗伤寒用药,华佗云:“若无丸散及(雪)煎者,但单煮柴胡数两,伤寒、时行,亦可服以发汗,至再三。”仲景明显就完全反了过来,首选汤,无汤可丸散:“凡云可发汗,无汤者,丸散亦可,要以汗出为解,然不如汤,随证良验”。说明以汤易丸散是基于疗效的考虑。汉末《伤寒论》汤剂的忽然成熟,发育时间并不长,似乎更象是突变。从前面的比较分析看,仲景方用汤和泛用甘草,两者效用具有一致性,或许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
在印度医典《医理精华》中,论热病治疗,首论断食(可以喝柠檬水之类)。然后第一个药物就是热开水(因痰和风产生的热病)。在新热刚起时,《医理精华》重点在服用增加体液的药液(汤药),而不是重点在发汗,这个和现代医学的应对差不多。此书未专论发汗,但在《医理精华》第26章眼科的“头部疾病”部分,提到一种中医熟悉的发汗法:“(对于风性头痛症)应该服用混合汤(由稻米芝麻绿豆等所熬)或服用牛奶加上稻米等能驱风的那类药物,使头部发汗。”在印度医典《阇罗迦集》第14章中,全面论述了发汗法,其发汗法,目的只是先使病素处于流动状态(病素显在化),便于后续采用适当的排除净化法。印医的发汗法基本属于物理发汗法,方法多样而繁杂,且发汗之前先使用油剂涂身,使“风”得到抑制。发汗法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火的特性的发汗13法 :温湿布或袋子(内有药物)发汗法;床上温湿布覆盖发汗法;导管蒸汽发汗法;药液喷洒发汗法;浸浴发汗法;“火之屋”发汗法;卧热巨石发汗法;炭沟发汗法;小屋烤炭火发汗法;热地面发汗法;药液蒸汽发汗法;土穴加热发汗法;燃粪烘烤发汗法。第二类是基于非火的特性的发汗法10种:运动、暑热、厚被、空腹、饮酒、恐怖、愤怒、争论、太阳晒、温湿布。可见其法何等繁杂。这类印式基于火的发汗法,不知跟仲景方中所谓的“火劫”有无关系? 传说“保胃气,存津液”六字诀是清代陈修园从《伤寒论》中总结出来的,大概是个误会,陈修园读《伤寒论》只总结了一个三字诀“存津液”:“长沙室,叹高坚,存津液,是真诠”(《医学三字经》)。他认为存津液为《伤寒论》之要,此论颇得后世医家赞许。近来又有医家发挥,认为甘草是为保津液之载体,仲景方以保津补水的甘草做主干构建,此说颇新颖。我觉得,或者,热汤+甘草的组合才是仲景方最基本的方根,保津液的载体。血液和津液是生命之本。保津之说颇符合上古人类朴素的生命观,动物血流光了就死了,树干枯了就死了。而热、冷(风)都能导致草木干枯。这正是上古初民对自然生命的朴素常识。
我注意到《阿维森纳医典》(约1020—1037年)中提到,除意外之外,伤害人体生命的原因有二,一是身体的“湿”被干燥;二是体液发生了腐变。生命产生于男女湿性物质,生命就是一个身体逐渐“干燥”的过程,直至死亡,如同油尽灯枯。摄生的关键就是保“湿”调“湿”。换成汉语,大概就跟保津液、调津液差不多。可见东西方传统医学思维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参见《阿维森纳医典》第三部分《摄生法》。
经方草枣蜜饴四甜中,最常用的是草枣蜜,我列表比较其效用,四者相类,而草枣两者最相似。从本草效用的特效点看,蜜、饴突出是补虚;甘草是解毒;枣能定大惊。但异常的是,仲景处理大毒并不用甘草或胶饴,而是用蜜(如蜜煎乌头、甘遂等)和枣(如十枣汤),蜜枣都是甜料,这与印度医学、藏医学以糖、蜜剂解毒而不用甘草有相似之处。以蜜、枣处理大毒药物可能属于比较原始的汉医学技术,出现在甘草泛用之前。汉代《本经》中,“石蜜”(蜂蜜)就明确有“解药毒”的功效,而《本经》“大枣”条,明确说“和百药”。仲景方中药物比例,存在枣的用量相对特偏大的现象,不好说是不是原本存在调口味意思。甘草也叫蜜草,丸用枣、蜜,汤用甘草,也符合一种合药传统的演进。据此我推测,甘草在东汉兴起的解百药毒的新功效,也可能是对传统枣蜜解药毒的一种低成本平民化替代所发展出来的,怀疑东汉与西域的交流中,有大量的西域甘草流通到中土,西域商人或许还对甘草的药效进行了某些夸张化的商业宣传,这种戏码在后世药商推广行销中一再上演。
汉方医学的传统中,人造糖从不是主流药物,仅仲景建中类汤中用胶饴,而汉代《本经》中是没有“胶饴”条目的,到陶弘景《本经集注》才收录“胶饴”,应是引自《名医别录》,应该也主要是因为仲景在建中类汤所用。“西国石蜜”(块砂糖)虽在汉代已经流入中土,但仅为权贵奢侈品。而“石蜜”(块砂糖)和“沙糖”在唐代《新修本草》才收录成条,虽然唐代中土制造沙糖的技术已经领先,产量应该也不低,但蔗糖一直也没有成为重要的药物。这与印度医学方剂好配糖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
二、东西方药效交流之迷
甘草属植物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暖温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北纬36-57 º,东经0-126 º)。由于甘草的枝叶是一种优良的饲用牧草,人类与之打交道极早。按常理,甘草这种甜根无疑很早就会被人类所认识和使用。甘草在东西方入药都很早。(因为西方医药史资料中文版罕见,以下西方甘草的药用史料难以保证准确性)
据说两河流域的上古文明已经使用甘草,记录在泥板书上。传说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公元前1770年左右)中就记载有甘草,但查看法典原文却没有相关内容,应为误传,或是对椰枣的误译。公元前1000年的埃及纸草书中记载了甘草治疗呼吸道炎症。在古埃及图坦卡蒙(Tutankhamun,公元前1356年至1339年)的墓葬中(1923年出土),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非常完好的大量甘草贮藏(一说是光果甘草种子)。公元前7世纪左右,古希腊人从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人)那里学会了使用甘草,斯基泰人是人类史上第一代游牧霸主(欧亚草原西部),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基泰人可能是从新疆一带西迁的,为强秦所迫。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记载甘草有疗溃疡和止渴的作用。西欧“植物学之父”泰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287年 古希腊哲学家)在其所著世界上第一部古代植物分类著作《植物学史(Historiaplantarum)》(或《植物的研究》)中记载有甘草,称为赛西亚草,说在黑海沿岸大量生长,将其含于口中,可起到去火止渴作用,并提到这种草根的甜味成分可安全地用于糖尿病患者。还称:“斯基泰人可以12天内不饮水,因为他们咀嚼甘草和食用马奶乳酪”。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前323年)和罗马的凯撒大帝(公元前102年—前44年)都曾命令他的军队在长途跋涉中咀嚼甘草,以缓解因缺水造成的口渴及增强士兵的体力和耐力。”据说二战时期,法国和土耳其士兵的军用背包中也都备有甘草根,不知确实否?(如今法国某些地区民间仍有将甘草根当成口气清新食物直接嚼食的习俗)
印度传统医学认为甘草对咽喉有益(比如清喉咙),将它与温牛奶冲兑,可作为救心丹。还认为甘草可以起到净化血液、缓解腹痛、益智健脑、甚至美肤美发明目的作用(即印度古代医学文献《闍罗迦集》记载:“甘草有增强视力、精液、头发、声音、皮肤和血液的作用”)。他们还常将甘草与与催吐果等合用,用于催吐(此用甘草或不是为了催吐,汉医学早期也认为甘草能催吐)。在寒冷的北欧地区,甘草被视为治疗伤寒、黏膜炎、肺病必不可少的基本用药(何时开始有此认识不详)。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部分地区的土著中,至今仍有含嚼甘草的习惯,称为“甜棒”,谓可防病。古埃及、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甘草作为当时常用的药物之一,他们把甘草用作强壮剂,并认为可冶咳嗽、哮喘、喉痛、伤口、溃疡、伤风寒,不孕不育,可止渴,可用于镇静内脏(中医有治疗“脏躁”的甘麦大枣汤),也也被用来治疗 “dropsy”——小腿与脚踝的浮肿症(糖尿病?)这些大略与汉医学是相同的,但甘草在汉医学中较为特异的就是“解百药毒”了。西方传统医学非常重视解毒剂的配置,著名的如古希腊的底野迦、印度的阿伽陀丸,甚至还有一些解毒剂专著,但似乎都没见特别推崇甘草的解药毒效用的。
中国对甘草的药用到底有多久远?《诗经》(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中有“苓”,旧释为甘草,恐非。西汉《神农本草经》中就正式收录了甘草。4000年前的新疆罗布泊小河文化的墓葬中出土有芦苇、骆驼刺、麻黄、黑果枸杞、胀果甘草、牛胶(古阿胶)、代赭石等,因气候干燥,大多保存良好。对出土干尸头发进行分析表明,富含麻黄碱、伪麻黄碱等元素,表明先民对麻黄的摄入非常普遍,不仅是药用,可能还有一定宗教意义。可惜没见针对甘草进行摄入分析,所以也不能确定小河人有没有药用甘草。我们知道汉代《伤寒论》中,麻黄剂多是配用甘草的。DNA研究表明,4000年前,小河人的基因是东西方人种混合的,父系普遍是西方谱系,母系是混合的。虽然东方谱系所占比例非常高,但多样性低,说明其中有家族特色。因此,这种混合模式应该源自通婚而非战争。而且从东方过去的女性在墓葬规格上看地位较高。西方的六倍体小麦与东方的黍也在小河共存。普遍摄入麻黄的小河人有没有可能混合着甘草药用?如果擅长药用甘草的斯基泰人确实也是从新疆地区西迁的,则更有理由怀疑西域一带可能也是人类甘草药用的祖源地或文化原点之一,进而逐渐向西向南向东扩散传播。
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曾出土有以甘草叶为芯的头枕,年代约东汉魏晋。17世纪新英格兰农业作物学家兼兽医杰维斯·麦格翰曾说“甘草在治疗马类疾病方面疗效卓著”。巧的是传说黄帝时的马医马师皇用“甘草汤”为龙治病(《列仙传》),而中国商代晚期忽起的家马和牧野之战中姜子牙带头冲锋的马匹战车技术,很可能是西来的,最早使用甘草汤的马师皇会不会也是西方来的异人?虽然晋人葛洪认为所谓“列仙”都为妄造人物,但或许多少隐含着历史的痕迹。近年正在发掘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古城遗址(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之间),就目前核基因组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石峁人群与甘青地区人口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从已知史料看,上古时代,西域一带、欧亚草原西部、埃及、希腊等地区的甘草药学知识,比中土更古老而丰富。鉴于东西方传统医学中甘草效用的相似性,是否意味上古时代存在医学知识上的交流?虽不敢说定有,更不敢说绝无。从近些年的新疆及西部考古揭示来看,远古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通远超以往人们的认识。公元前500年至公元200年是人类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时期,很多原产于西方和东亚的药物、香料开始了远途的国际贸易。我看多尔比《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虽然书中提到丝绸之路上有甘草向西输出,但全书却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史料,无法估计这种东西方都有的甜根在古代有多大国际贸易的价值。但因为甘草“止渴”的效用,我怀疑它可能是丝绸之路历史上长途跋涉的客商的必备物资。
在中国科技史上,汉代是一个科技发明的爆发期。这种爆发很可能跟各种文化的大交流有关,或者是一种催化。汉武帝时,破匈奴通西域 凿空东西,开西南夷道交通印度,灭南越置九郡,以及汉代印度佛教的传入,都必然带来文化、医学的交流,汉代无疑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碰撞的时代。当其时,埃及的亚历山城是西方的文化和学术中心,群贤毕至、盛名远播,也是丝绸之路西端的终点站之一。而古埃及的医学不但有发达的经脉学说(上下肢体各6 条),也擅长使用甘草疗疾。这类知识也有可能随商旅在丝绸之路逐站东传。
综上所述,甘草的泛用应该始于东汉时代。西汉之后本草经中的甘草,功效增加了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安和众草石等功效。经脉学说是东汉的医家显学,甘草“通经脉,利血气”之说出自东汉不奇怪,“开通经脉”或许是当时的一个医疗思维重点。古埃及、古斯基泰人、古希腊人以甘草治喉痛、咳嗽、哮喘,并特别强调甘草的止渴功效,可能在西汉破匈奴通西域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对汉代医学产生了影响。古印度医学中,甘草增精力、使体肥、治大出血、治创疡、疗渴、净化体液血液、救心。这些功效与《本经集注 甘草》的相似性很高,印度医学随着汉代印度佛教的传入,可能也对汉代医学造成了某些影响。除了直接文化传播的影响,外域医学文化可能还存在“激发传播”式(思路启发)的影响。
三、宋以前非调味品之迷
甘草在西方很早就是药食同源之物,据说古埃及法老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饮料“麦舒(Mai sus)”就是利用甘草制作的,是国王与贵族阶层的特供饮品,如今在埃及和叙利亚等地依然是流行的大众饮料之一,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有小贩背着一个大铜壶、挂着几个杯,沿街叫卖甘草饮料。古老的印度教认为甘草是创造宇宙之神梵天(Brahma)所喜爱之物,其教徒认为,喝甘草、牛奶及糖调成的饮料,会增强性欲。古代希腊人煎煮甘草汁,脱水浓缩得到黑色甘草糖浆(浸膏之类),后来发展还掺入少量淀粉,倒入模具制成黑条状或块状甘草膏,印上制作人的姓名,干燥后出售,在热天也不致溶化。他们用甘草浓缩物进行买卖交易,这种物质的交易最后遍及整个罗马和中欧。一直以来欧美不但利用甘草制作饮料、在甜点、酒、菜肴中调味,还专门制造甘草糖果,黑甘草糖大约诞生于200多年前的北欧,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传统产业,在德国、荷兰、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很受欢迎,消费量很大,最基本的甘草糖,原料是甘草膏或精粉,加上淀粉或明胶,溶于水中,加热至135摄氏度,倒入模具即可,成品外表为黑色。虽然是甘草糖,可欧洲人多喜欢偏咸味的(含氯化铵)。洋甘草也曾被美国的烟草行业用来为烟草调味,但在2009年被禁止了。在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和法国,如今民间仍有将商品甘草根当成口气清新食物拿来直接嚼食的习俗。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地区,流行一种纯用甘草根酿成的传统利口酒,算是当地特产。
不知是不是因为中国发明饴糖早,唐代以前几乎不见甘草被应用于食品加工中。《礼记 内则》:“枣栗饴蜜以甘之。”没有用甘草。《齐民要术》中的食品加工也未见用甘草。大概到了宋代饮食中才较常用到甘草。宋人风俗“客至点茶,送客点汤”, 宋人 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 温或 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从苏颂《 本草图经》看,用于点汤的甘草大概多用下等货色:“其轻虚纵理及细韧者不堪,惟货汤家用之”。其实这种保健类的“汤”是以甘草和盐、姜共同调味(大概偏咸),基本都为粉剂沸汤点服,与点茶法相同,其不论调味还是冲服法都模仿了当时的饮茶。宋代之后,中国烹调、零食、蜜饯制作中使用甘草才渐多。现今潮汕、化州等南方地区,民间流行小食“甘草水果”(新鲜水果用各种调料拌食或蘸点而食),遍布大街小巷,此或是古遗风。如今新疆也有厂家生产销售甘草酒、甘草饮料。
甘草这种甜根,按常理,人类对其利用最早很可能是用以食用或调味的。何以在蜜和饴糖都不便宜的唐代以前,中土见不到其用于调味的史料?史料湮没了吗?这始终是一些可疑的问题。当然有很多种可能。
四、其他
甘草是山羊豆族甘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境是荒漠草原、沙漠边缘和黄土丘陵地带。甘草属植物学家李学禹教授等人的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不仅甘草种数集聚,新种与新变种多,变异多态现象复杂,且所有种都含有甘草甜素。表明此区域应为世界甘草属植物变异多态分化中心。参见《甘草属(Glycyrrhiza L.)分类系统与实验生物学研究》。我国目前药材甘草的主要原植物为乌拉尔甘草,药学史家考证后认为我国古代药用甘草主要也是这种广布种。
甘草耐寒耐旱抗风固沙土,再生能力旺盛,沙土中只要留有残根就能发芽,根系极其发达,可在地表以下数米处呈水平状向老株四周延伸形成纵横的地下强大根状茎网,随沙层覆盖度的增加,还可形成上下3~4层根状茎层,以保证获取自身生存所需水分。它的这种种生命特征,或许会影响“医者意也”的古人对它药效的“认识”。甘草嫩枝会散发一种奇特的气味,荒漠草原的食草动物对这种气味异常敏感,当空气中飘散着这种气味,则预示着苦尽甘来春天到了。今宁夏清真菜中,甘草嫩芽是可以作菜吃的。甘草的多年老主根还可制为手杖,司马光就有此物,见宋 梅尧臣《司马君实遗甘草杖诗》。
甘草是人类最古老的药用植物之一,至今仍是世界最有价值的传统草药之一。甘草的人工栽培较早。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向欧洲扩张时开始在西班牙种植甘草。15世纪中叶(1450),德国法兰克福地区开始有人种植,后来巴伐利亚地区也出现了甘草种植园。16世纪中叶,甘草在英国成为重要的作物,种植于约克郡的庞蒂弗拉克特镇、诺丁汉郡的沃克苏普一带(英格兰西约克郡目前仍然种植甘草,供应全国)。目前印度有甘草种植,但品种与我国不同。据说目前在俄罗斯、西班牙、伊朗都有甘草栽种,规模如何不清楚。美国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种植有一些欧甘草。我国目前是世界甘草及其提取物的主要供应国。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甘草人工栽培的研究。近些年由于掠夺性的野蛮采挖,我国西部野生甘草资源已经陷入危险境地,结果催化了我国甘草的大规模的种植,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甘草中约有20%是人工种植。因为国内采挖管制趋于严格,目前我国新疆口岸在大量进口邻国的野生甘草。
附一: 如今阿育吠陀、藏医、蒙医的常用方剂中使用甘草的频率如何?孙铭《印度阿育吠陀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药物制剂对比研究》中,从中印两国的药典、部颁标准、方剂教材等提取各传统医学最常用的一些方剂(成药)分析,阿育吠陀645方成药,最常用50味药物中,光果甘草使用频率排名第14名,占比是17.8%(排名前五是荜拔、姜、诃子、胡椒、余甘子)。藏医458方成药,甘草/甘草膏使用频率排名第20名,占比是14.85%(排名前五是诃子、红花、木香、豆蔻、余甘子)。蒙医164方成药,甘草使用频率排名第20名,占比是13.4%(排名前五是诃子、红花、栀子、石膏、豆蔻)。
参考资料: 史丹利 《对四逆汤中何以用甘草而不用大枣的思考》 多尔比《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 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
| 

 窥视卡
窥视卡 发表于 2021-9-2 12:05:23
发表于 2021-9-2 12:05:23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发表于 2021-9-2 14:31:18
发表于 2021-9-2 14: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