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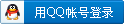
x
本帖最后由 15119466652 于 2025-4-16 09:06 编辑
证的逻辑(东洋医学的特质)治疗方法的多样性
反观现代医学,即便面对胃溃疡或神经症这类无论哪位医生诊断都不会出错的病名,实际使用的药物却因接诊医师不同而各不相同。即便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接受诊疗,虽然病名相同,治疗药物也绝不会完全一致。 此外,还会产生流派性差异。面对化脓症状,古方派医家认为是葛根汤的证,而经验派医家则主张应属十味败毒散的证。 方证相对
古方体系中的葛根汤有其基于古方立场的方证对应法则,经验方的十味败毒散亦存在基于经验方立场的方证对应法则。方证对应学说的本质精神在于,无论古方、后世方或经验方,处方的适用证均有其严谨标准。但当这种标准被偷换为流派优劣之争时,便会产生认知混乱。 针对"证唯一性"的讨论,间中喜雄先生提出了极具价值的观点:"把握某个证的方法并非是绝对唯一的。正如蒙田的箴言所述:人类常通过不同途径抵达相同终点。"(《汉方临床11-11·关于证的反思》) 证简单来说就是适应证(indication),而构成它的则是适应症状。适应症状的数量被认为是多个,因此被称为复合症状或症候群(综合征),但单一症状也未必不能称为证。桂枝的证、柴胡的证等就是例子。由肾阴气盛引起的奔豚、腹动、动悸等上冲,仅仅因为是上冲,就可以成为桂枝的适应证。当然,这也在言外包含了并非肺上气、肝撞心、胃上逆等情况。说到上冲,就意味着不是上气。胸胁苦满则意味着是柴胡的证,尤其是小柴胡汤的证,但这也在同时表明了并非大柴胡汤的心下急、柴胡桂枝汤的心下支结、生姜泻心汤的心下痞硬、木防己汤的心下痞硬等情况。急迫则用甘草,呕(并非吐)则用半夏,更简单地说,可以将适应症状作为证,例如“这个化脓是桔梗的证”“这个心痛是薤白的证”等。 试图仅通过症状来构成证的是江户古方派及其追随者,而我则试图结合状态和病理——甚至追溯到病因进行探讨(参见后文“原因的思考”部分)。 通常会有胸胁苦满,但偶尔也可能不明显。即便如此,如果寸脉涩、尺脉弦细,也可以认为是小柴胡汤的证。如果是大柴胡汤,则会有心下急或脉沉实。柴胡的证只需确认一个症状即可(可能符合《伤寒论》太阳中篇第二十条)。柴胡的证不会仅仅表现为咳嗽或黄疸。咳嗽、黄疸、呕吐、食欲不振、腹痛等并非必然症状,而只是有可能性地出现,因此被表达为“或”呕吐、“或”咳嗽等。 在使用小柴胡汤或柴胡桂枝干姜汤时,如果出现瘙痒,会将其视为心烦或黄芩的证而使用这些处方。那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明确写上瘙痒呢?答案是否定的。 决定证的适应症状需要从自觉和他觉症状、脉象、腹诊所见、经络的变动等各方面获取所见,并进行选择性的取舍。如果病变仅限于局部,且尚未在其他症状或脉象上出现所见,则只是局部变化,应进行局部治疗,此时尚未形成通常所说的证。在这个阶段,全身性的症状尚未出现。例如,息肉或动脉粥样硬化等良性肿瘤,即使是癌症或肉瘤的极早期,或者小的脓疱、化脓症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此外,所见症状过多或过少都会带来问题(参见拙著《汉方医学概论》再版第44页,已绝版)。正如已故的长浜善夫也曾提到(《汉方的临床1-1》),所见症状过少的情况,例如蛋白尿时,往往是因为汉方医学的自觉和他觉症状较少,或者汉方医学的技术水平不足,导致无法准确把握所见。 证的字义与用例
然而,太阳病中篇第221条“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云云”以及第220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者,但见一证便是”,上篇第145条“证象阳旦云云”中,“证”不仅指症状,还包含了柴胡剂或桂枝汤类药物的适应证的含义。由此可见,在《伤寒论》成书的汉代,由于尚未有“症”字,“证”既用于表示症状,也用于表示适应证。这种用法后来发展为江户时代古方派所主张的适应证的含义。 此后,中国除《证治准绳》外,几乎没有使用“证”字的例子,也未发展出“适应证”的含义。《证治准绳》以症状而非脉象作为确定处方的依据,其“证”仅用于表示症状,这一点不言自明。 客观性和他觉性所见的代表是脉象和腹诊。在中国医学中,脉象往往被过度思辨化,缺乏从事实中归纳的实践。然而,古方派并未对其进行修正或重新审视,而是完全回避了脉象。但取而代之的是重视腹证,其代表作《腹证奇览》及其续作《腹证奇翼》便是这一思想的成果。在腹诊中,腹部所见被称为“腹状”,当其成为处方的适应证时,则被称为“腹证”, 以此加以区分。 诸家之说
B. 仅凭症状构成证的状况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并非杂乱无章地排列的,而是经过整理分类后加以研究的。例如,脉浮是表脉,表示“部位”;发热和恶风则是热象的表现,表示“状态”。仅凭这些还无法区分是麻黄汤、桂枝汤还是葛根汤,但因为有项背强,所以可以确定为葛根汤。项背强虽然是表示状态的症状,但在这种情况下,它起到了类证鉴别的特殊作用。 脉浮、头痛、发热(这是表证的表现,表示“部位”)、胃内(部位)有水停滞(状态),口(部位)感到干渴(状态),胃(部位)出现呕吐(状态),小便的排出(胃与膀胱的部位)不畅(状态),C则是将症状与状态组合而成的。在日常实践中,这种程度已经足够,但有时也需要更加复杂且理论性地思考病理。 由于背部恶寒且脉象沉弱,可以考虑附子汤,但因为存在下利的症状,改用人参汤。这是因为两种处方的性质相近。 患者常诉说受风邪感冒后常出现此类症状,此因阳气虚弱,所以易感外邪,且背部也容易感到畏寒。 列举现代医学病名并根据症状选择处方的做法虽属基础方法,却是当前医家们的普遍实践。 这个症状abc是指汉方医学的症状,不包含现代医学的理化检查结果。这里虽然没有像CD那样的纯粹汉方,但存在兼具汉方特色且易于从现代医学入手的途径。 综合征
近来,倾倒综合征、肾病综合征、吸收不良综合征、脚气病综合征等以综合症命名的病名显著增加,实属必然。这反映出从病理解剖学框架中解放出来、试图立足于功能性病理学立场的一种倾向,但其主要目的仍在于确定病名,与汉方医学的"证"在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 证的定义我对证的定义
作为定义(证的辩证法结构、日本东洋医学会论文集、汉方医学讲义笔记)。 在现代医学中,一般重视普遍性,即普遍适用性,例如胃溃疡或阑尾炎等,即使在胃溃疡中也有疼痛的患者、吐血的患者等,患者甲与患者乙所表现的症状各不相同,如果不明确这些差异,就无法从(汉方)治疗角度具体判断应该对“此患者”使用生姜泻心汤还是黄土汤。现代医学以共同的病理解剖学变化和症状为基础,主要着眼于疾病的认知。现代医学常会忽视或舍弃“此患者”,而将重点放在胃溃疡这一普遍概念上。 例如,将腰痛视为肾虚,即因肾虚引起的腰痛。腰是部位的范畴,虚是状态的范畴,提到腰痛时不可以将其与肾虚普遍看待。因为肾虚中不仅包括腰痛,还包括小便不利或自利、阴痿、上冲等症状,而腰痛只是肾虚中的特殊个例。 高桥晄正先生著作的《汉方的认识》是我读过的汉方相关书籍中最令我感动的书籍之一。虽然受教之处不止一二,但与我原本的想法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有四五处。例如,个体差异的评价问题(同书161页)就是其中之一。 在没有肺炎这种普遍病名的时代,汉代医学通过汉方的诊断方法,个别地识别症状和汉方病理等,根据掌握不同的状况下的本质,并作为小柴胡汤、真武汤、竹叶石膏汤等证进行治疗。 然而,这种情况仅适用于由病原菌引起的某些传染病,而对于胃下垂或肾病综合征等普遍病名,是否也有通用的治疗药物呢?无论是胃下垂还是胃溃疡,汉方通过个别化的治疗几乎可以达到100%的治愈率。 仅凭普遍的病名或所见——例如胃溃疡、虚劳或黄疸——如果不进一步结合个别化和特殊化的内容,汉方是无法进行治疗的。 确实如此,现代医学倾尽所有知识来检查每一个所见。但是,如果血液中的钾增加或减少,汉方会如何处理呢?应该用表里、虚实、寒热、气血水等范畴中的哪一个来处理呢?如果小便中的蛋白质增加,处方会如何变化呢?如果X光或心电图出现一定的变化,这会对汉方的病象和治疗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汉方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全部无关。而无关的因素,在汉方的立场上目前是不予考虑的。 尽管如此,未来必然会提出以现代医学知识来理解、解释和表达汉方的要求,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接着我们继续探讨,“现在”的状态是由体质、自然病程以及过去治疗的结果等引起的。即使是明确的葛根汤适应证,如果给予葛根汤,葛根汤的证虽然得到缓解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发汗过多,出现了桂枝加附子汤的证;或者表证虽然消除了,但热邪入里,变成了小柴胡汤的适应证(《伤寒论》卷第十,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更何况误治的情况下,原因导致结果,结果又成为新的原因,引发新的状态,正如《伤寒论》中反复提及的那样。 然而,现在并不会永远停留,而是每时每刻都在成为过去,同时也在每时每刻创造未来。因此,过去与未来通过现在相互联系,正如历史哲学所阐述的那样。原因成为结果,结果又成为原因。我们必须观察时间上连续发生的状态,并针对其进行治疗。我们不能将病态视为静止或固定的存在,而应将其看作不断变化和流动的过程,并在某一瞬间抓住这一过程的一个断面。如果不加入“现在”这一时间契机,就无法把握住证候。 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现象与本质是统一的。例如,咳嗽在现代医学中仅被认为是从呼吸器官发出的,而在汉方中则认为与心、肺、肝、脾、肾等脏腑有关(《素问》第三十八,咳论)。确实,有心性咳嗽如灸甘草汤,肝性咳嗽如大小柴胡汤,脾性咳嗽如真武汤,肾性咳嗽如苓甘姜味辛汤。咳嗽是现象,但引发咳嗽的疾病本质在《素问》中被认为与多种脏腑有关,这就是其理由。 相互关联
从作为现象的症状中可以推测本质(如太阳病、少阳病等),但由某一本质引发的现象性症状并不一定仅限于头痛,也可能表现为恶寒、脉浮等数个症状(现象)。这里存在不确定性、自由联想,以及处理时的主观选择性,因此也可能出现误判。 病象并非直接描摹的客观所见本身,而是通过医师的主观思考介入,将描摹与构成相结合、构成与描摹相统一后形成的观念形象。正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形象,反而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具体的客观性。证与现代医学中的病名不同,并非将病理变化的认识进行概念化,而是在“证”本身中直接统一了汉方的诊断与治疗,这是其特征所在。 在名称与实体之间存在实体论与唯名论的问题。实体论是指,当提到病名时,其病理、症状、经过、转归等会立即浮现,病象会在医生的脑海中描绘出来。比如提到肺结核或胃癌,就能大致想象出其特征。唯名论则认为,病名是一种被抽象和构成的观念,并不是对实物的直接描摹。两者孰是孰非可能因立场不同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但现代医学倾向于实体论的立场,而汉方医学则更接近唯名论的立场。 汉方中,会将现代医学中可能被舍弃的症状——例如口渴、胸胁苦满、腹动、咽中炙脔、足冷等——提取出来,将个别的、特殊的症状原封不动地采用,不构成抽象的病名,而是构成具体的病象。然而,由于表达方式基于汉方的病理学或症候论,并使用汉方的范畴,因此这一点也必然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即使是同一个现代医学病名,如胃溃疡或肾炎,如果汉方的病象因个体差异而不同,则证也会随之不同,治疗(处方)也会不同。因此,汉方的立场并不拘泥于现代医学的病名。不拘泥并非否定或排斥,而是与之无关的意思。然而,将无关的事物——现代医学的病名与汉方的治疗——联系起来的地方,正是对病名治疗的特殊意义所在。 以病名为对象治疗
在这种立场下,对于无法确定现代医学病名的情况、因医生不同而诊断各异的情况、即使知道病名但对这种疾病经验不足的情况等,该如何处理呢? 最终,以现代病名为对象的治疗是现代医生的立场,而汉方并不存在。 证的范围
但我将证的意义扩大,不仅将其局限于处方的适应证,还广泛地将病象本身视为证。这种病象中包括无法成为处方适应证的死证和不治之证。证无需对病象进行任何操作或处理,可直接转化为适应证(拙著《汉方医学讲义教材》关于证的章节)。 1.不将证仅限于处方的适应证,而是扩大其意义,直接指病象本身。即广义上指病象,狭义上指适应证。 2.我还指出,病象会“转化”为适应证,明确区分了两者。藤平健先生认为“如果仅收集有关医生诊断的,患者的客证,无论如何都难免片面性”(《关于证的两面性》,《汉方的临床》13-7-35),并基于奥田谦藏先生的学说“证是身体内部病变外现的征候,借此说明疾病的本质(龙野注:以上为A),或(龙野注:加点)以此为药方立证(龙野注:以上为B)”,指出证具有两面性。 3.与江户古方派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江户古方派仅提取症状,而我则同时提取状态和病理。 在确定证并进行治疗时,表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认为这是最合适的治疗,便是“主之”。可以说是绝对指征。 “宜”是指桂枝剂或柴胡剂的处方群,或是发汗、吐下、温补等治疗方针大致已定,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必要的条件,从类方中选择适合的处方使用。例如,“宜桂枝汤”就包含了桂枝加葛根汤、桂枝附子汤等桂枝汤的同类方剂。 “宜四逆汤”则包括四逆汤类、通脉四逆汤类、干姜附子汤等同类方剂。 例如:“伤寒,阳脉涩,阴脉弦者,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太阳病中219)便是如此。 例如:“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痰饮210)。茯苓杏仁甘草汤与橘皮枳实生姜汤、越婢加术汤与甘草麻黄汤也是其例。 小青龙汤、小柴胡汤、四逆散、真武汤等适应症状中,有“或”什么、“或”什么的记载。例如: 仅从症状考虑会感到混乱,但从病理考虑则能理解。 若仅仅列出咳嗽、小便不利等症状,彼此之间似乎并无关联,但如果考虑病理,就会发现这是因为肝的变化导致气聚集于局部,气无法上下流通,从而引发四肢厥冷;肾的阳气衰弱,阴气盛行,并进一步影响到与肝相关的脾胃及心小肠,最终引发上述症状。这些症状并非同时全部出现,而是有的涉及胃,有的涉及心,表现为时隐时现,因此用“或”来表示。此外,这些状态和症状都与各药物的作用密切相关。 这种“或”的关系,即可能发生的变化与能够治疗的可能性的药物组合,在各种处方中经常可见。例如,葛根汤既可适用于 “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同147)。项背强与自下利在症状上看似没有关联,但项背强属于肌肉,肌肉属胃,下利也是胃的症状,葛根的味甘平,甘属胃,因此葛根可以同时作用于项背强与下利。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少阴病434)以及 这两条条文。是否可以从这两方的适应证中任意选取症状,然后使用真武汤?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有些情况下则不行,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在少阴病的状态下,出现发热、小便不利、心下悸、头眩,或发热、咳、小便不利时,可以使用真武汤;但如果出现小便不利、振振欲擗地,则可能是苓桂术甘汤或泽泻汤的适应证。三者可通过脉象或其他症状来区分,真武汤的脉象为沉弱,苓桂术甘汤的脉象为沉紧,泽泻汤则有支饮症状。这是适应证不一定完全合适的例子。 在许多症状中,必须判断出主证和客证。这是为了整理症状和确定适应证的必需。现实中,症状往往非常多,其中甚至包括像三物黄芩汤的“头不痛”这样有意义的阴性症状,如果再加上现代理化学检查结果,症状的数量将变得极为庞大。从中提炼出主证,最重要的线索是主诉。然而,当主诉过多时,需要审查是否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一种或两种状态。例如,患者诉说偶尔腹泻、腹痛、足冷,可能是胃寒伴有水饮(分泌过多),可能是人参汤或真武汤的证,主证可以推测为胃寒和水饮。其他症状中,人参汤以寒为主,小便自利的状况较多;真武汤以水饮为主,小便不利的状况较多。 以上这样的症状、症状群,通过治疗经验、处方解说或个人经验来辨别。 由此可见,主证和客证有时会转换位置。 君臣佐使
后世方的加减或部分古方家的加减只是添加,几乎不减少。因为减少药物要困难得多。 葛根汤(君药)葛根(臣药)麻黄、桂枝(佐药)生姜、甘草、芍药、大枣 四逆汤(君药)甘草(臣药)干姜(使药)附子 君臣佐使超出了本稿的主题,因此不作详细说明(参见《汉方研究》——君臣佐使,《汉方的临床》14-5 用药相关的二三原则 君臣佐使)。 例如,四逆加人参汤中,处方中最初的甘草是主药,治疗胃虚和寒盛导致的恶寒或四肢冷,脾虚导致的血虚和亡血。因此,主药是甘草,主证是脾胃虚。 当被问及将许多生药混合在一起,很难回答哪个是君药,但根据药物在处方中的作用意义进行价值判断,从而确定其君臣佐使的地位。然而,这种价值判断不是针对药物种类,而是针对药物的功效,从四逆加人参汤和茯苓四逆汤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随着处方的不同,君臣佐使的地位是可以转换的。 多个症状
非常初级的做法是,例如拙著《汉方卡片》第二辑(绝版)中关于头痛的确认要点的各条文,吴茱萸汤的条文中写有呕吐。同书中关于呕吐的确认要点条文写有“呕吐时头痛的”,处方便是吴茱萸汤,确认点中还有贫血、畏寒。无论是查头痛还是呕吐,都可以知道处方是吴茱萸汤。 在使用这些方法时,需要注意的并不是使用这个处方就一定能100%治愈疾病,当然也有治愈的情况,但有时疾病依然不动,有时会转化为其他情况。即"主之"的转归有一定的自由度。因此,有必要追查转归,这在拙著《伤寒论的研究》第三篇《伤寒论的结构》第十二节中作为"服后的转归"进行了说明。 验证
在汉方中,不能说"反正这种病只有这种药可用,谁来做都一样。之后的事就不知道了"。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处方的意义实际上也与此有关,如果使用准确,疾病应该可以治愈。 结束
例如,当肾的阳气衰弱,肾的阴气盛导致腹动、上冲等奔豚症状,这属于阴阳;肝(木)的热影响心(火)导致心烦,影响胃(土)导致虚弱,出现小柴胡汤的症状,则属于五行的变化。证的定义因人而异,似乎难以统一成一种标准。这与西方的一元论不同,似乎与东方的多神论世界观不无关系。(《汉方的临床》第十八卷第四•五合刊号) |